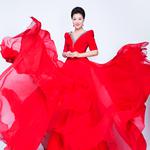本字幕由TME AI技术生成 偷鹅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 我们村里的人开始养鹅 我们那原本是没有养鹅的习惯的 这事儿的起因得从小头婶儿那说起 小头婶儿是铁匠老蔡从微山湖那边带回来的女人 老蔡叔说那地方养鹅养鸭的特别多 工业产品有竹编壳的微山湖牌暖壶 暖壶的商品名应该叫保温瓶 当时保温瓶是凭票供应的紧俏商品 后来我查了一下资料 知道了生产这个牌子保温瓶的厂家在藤县 现在那地方叫滕州了 退回去三十多年 当时的地方干部觉得把县改成市或州是一件很时髦很进步的事 一个地方如果还叫县 就仿佛这地方土气似的 其实改县为市是有成本的 单就那些党政机关 医院 学校 企业的牌子与公章的更换与制作 就是一笔很大的费用 其实山还是那座山 河还是那条河 土地还是那些土地 人还是那些人 改不改都一样 现在我看到那些还叫线的地方 反而感到特别的亲切 线字似乎透露着一种古典之美 当然 这古典之美里也包含着残酷与无情 朋友们查字典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当然 有的朋友不用查字典也知道我的意思 现在跨县 跨省甚至跨国婚姻都已司空见惯 但在当时 婚姻的范围很小 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一个村子里的人大都千瓜连腕的成了亲戚 我曾斗胆说过几句很可能引起争议的话 我说 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与思想的活跃 还带来了人的质量的提高 这话当然经不起严密的逻辑批判 所以也就过往言之吧 铁匠老蔡大叔从遥远的微山湖地区带回一个拖着油瓶的女人 这件事在我的村子里引起的轰动是可想而知的 那油瓶儿是个男孩 岁数与我差不多 我应该是村子里第一个与他说话的孩子 因此我们成了好朋友 我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 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 我叫解放 这都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事了 老蔡出身好 又有打铁的技术 他的影响力超出我的想象 连公社里的很多干部都与他有交往 所以他与那个女人的结婚手续以及迁移户口等在我们看来相当复杂的是 好像也没费什么劲儿就办妥了 现在回忆起来 这个来自遥远地方的女人其实是个美女 但在当时村人们的审美观念里 她的长腿细腰长脖子小头看上去相当不顺眼 因此大家给他起了一个绰号 叫小头婶儿 那年卖收钱 小头婶儿从他的家乡带来了一个赊小鹅的男人 说是他姨家表哥 那男人膀大腰圆 红脸膛 直鼻子 嘴里一口看上去很结实的浅黄色的牙 我们这里每年都会来赊小鸡儿的 但赊小鹅的还是第一次来 那人在村中央粗大的国槐树下支起了摊子 两大扁笼 毛茸茸的浅黄色的小鹅在笼子里拥挤着 沙哑着嗓子鸣叫着 村里的小孩子都围在树上看热闹 小头婶儿撇着吸线枪 替他表哥招揽着顾客 村里人没有养鹅经验 都犹豫着不敢说 蒋家那位面部有几个浅白麻子的大娘问小头婶儿 大婶子呀 你光张罗着让俺们吃 可俺用什么喂他呢 小头婶儿说 呀 小的时候掺和点玉米面喂喂就行 过几天赶到大湾里 吃鱼吃虾吃青草 什么也不用喂了 那男子也用浓重的吸线枪附会着说这玩意儿其实根本不用喂 赶到湾边去自己就长大了 小头婶率先垂范 自己赊了六只 赊小鸡儿的不帮人分辨公母 但赊小鹅的 将公的和母的分笼放着 要赊就赊一对儿 如果只想赊母的不舍公的 那是绝对不行的 舍鹅人的解释是 一公一母才能长大 单奢母的是养不活的 那年村子里有半数人家赊了小鹅 大多是赊一对儿 有十几户赊了两对儿的 小头婶家赊的最多 三对儿 凡动物 大多是小时好看 大时也好看 最难看就是半大不小时 鸡鸭鹅狗都是这样 鹅半大不小时 正是阴雨连绵的季节 村子西头那个长约二里宽约半里的大弯子积了很多水 像个小湖泊似的 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到湾里去洗澡 说是洗澡 其实是打闹戏水 我们村儿临河靠湾 村里的孩子水性都不错 但我们的水性与小头婶儿的油皮儿子解放比起来 那简直就不是一个等级的 他在大湾里展示了多种泳姿 惊得我们目瞪口呆 我问他 微山湖比我们这个大湾大多少 他皱皱鼻子 不回答我 后来我看了电影铁道游击队 才知道我的问题是多么可笑 村子里那些已经长得半大不小的鹅一天到晚泡在弯里 湾边有湿地 湿地里有野草和蛤蜊泥鳅之类的 鹅就吃这些东西 确实不需要喂了 有的人家的鹅黄昏时还知道回家去过夜 有的干脆不回家了 夜里就趴在草丛中或浮在湾面上 就像千人千思想 万人万模样一样 每只鹅也都有自己的样貌 每家儿的妇女与孩子都认识自家的鹅 鹅也都认识自己的主人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只外号叫歪把子机枪的公鹅 这只鹅是小头婶儿家六只鹅中的一只 这只鹅小时候脖子被黄鼠狼咬伤而留下残疾 它的脖子基部歪向一侧 头颈平行着前身而不是上扬 所以这只鹅的姿态仿佛随时都要发起进攻似的 它的样子的确像日本生产的歪把子机枪 这只残疾鹅性格暴烈 进攻性很强 在全村的数十只公鹅中 它是最好斗且美斗必胜的 因为它的残疾 造成了它进攻的诡异角度 令那些健康的鹅防不胜防 天气渐凉了 鹅也渐渐长成了 冬至那天 小头婶儿引领着他那位赊小鹅的表哥 按照当初记下的名单 串着胡同收鹅钱 即便那些没把鹅养成的人家嘴里发着牢骚 抱怨着小头婶儿 但也把钱还了 农历十一月 有的鹅开始下蛋 有的人家要办宴席 就把公鹅杀了招待客人 因为母鹅要下蛋 所以每天傍晚 养鹅人家的女主人或是孩子就会到湾边把自家的鹅找回家 但也有一些公鹅不愿回家 就停泊在湾子中央的蒲草与芦苇丛中 任凭主人呼唤 就是不上来 转眼进入腊月 天寒地冻 弯子里结了厚厚的冰 我们尽管白天还是要到田野里去干一些平整土地 开挖沟渠之类的活儿 但毕竟夜长昼短 又加上冰天雪地 所以一天也干不了几个小时的活 大家都不累 晚饭后就聚在六叔家打扑克 六叔是队里的会计 可以晚上记账为由报销两斤灯油 解放有一副小丑扑克 所以他每晚必来 算起来他来我们村儿也将近十年了 说起话来还有点西线口音 他跟老蔡姓 名字就叫蔡解放 打到高音喇叭播放国际歌时 大家都知道九点了 广播电台的晚间节目结束了 该是回家睡觉的时候了 这时一个人推门进来了 他是生产队里的保管员 外号叫曹草 他的真名我就不写了 曹操在民间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形象 尽管很多大人物写文章为他平凡 但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塑造的形象深入人心 大家提起曹操就会想到奸诈狡猾 诡计多端这些贬义词 后来为了称呼简便 人们便把这个本不姓曹外号曹操的人简称为老曹了 老曹进门后就摘下帽子 抽打着身上的雪 我们这才知道下雪了 看他肩头上积雪的厚度 知道雪下的很大 小个子方七对老曹说 您怎么才来 我们要散了 老曹说 别散呐 好戏还没开场呢 说着他就从腰里摸出了一个翠绿的酒瓶子 说 今天下午跟着老郭去蛟河农场喝酒 厂部炊事员老王悄悄的递给我的景芝白干儿 他举起酒瓶使劲摇晃了几下 然后将酒瓶子放在灯光下 让我们看瓶中那些飞扬的泡沫 而浓烈的酒香也从瓶盖的缝隙里钻出来 大家都贪婪的抽着鼻子 努力的嗅着酒香 可惜没有摇老曹说 六叔说 炒两个蛋行吗 老曹道 太行了 两个鹅蛋加上半颗大白菜 在炕角睡得迷迷糊糊的六婶说 哪里有鹅蛋是你下的鹅蛋个儿大 差不多每三个就有一斤重 方七道 算了 明天再聚吧 老曹 你先把酒放在这儿 明天晚上大家带着鹅蛋来 最少一个 多了不限 没有鹅蛋 鸡蛋也行 肉也行 鱼也行 哎 别算了呀 明天还有明天的局呢 哎 这样吧 老曹眼睛里闪烁着狡猾的光芒 说 小昌 解放 你们俩到大湾里抓两只鹅来 杀了煮煮吃 方妻道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老曹道 哎呀 漫漫的长夜 你急什么 我看看解放 解放看看我 心中都在犹豫 老曹道 怕什么 半夜三更的没人知道 解放道 只怕会留下脚印儿 方七道 正下着大雪 那留什么脚印儿 我说 大家必须保证谁也不说出去 老曹道 如果你们真能抓回鹅 大家吃了谁会说呀 哎 年轻人 干事国敢点儿 别前怕狼后怕虎的 我和解放交流了一下眼神 便一起往外走 老曹说 麻利着点儿 大湾北头那片苇地里有十几只鹅 我刚才路过时看到了 大雪纷飞的天气似乎不太冷 积雪辉映着空间 不黑 我和解放没有交谈 但我的心情怪怪的 仿佛要去干一件被允许的坏事 又像去干一件不被允许的好事 是不是 我们分拨开积雪的荆棘磕子 悄无声息的下到大湾冰雪上 冰上积雪格外平展 我们小心翼翼的往那片芦苇靠近 脚下的冰面发出一声脆响 吓了我们一大跳 那响声沿着冰面放射到很远的地方 鹅们似乎受到了惊吓 我们听到芦苇中传来几声悠扬的鹅叫 我们曾听人说过 鹅是由雁驯化而来 因此存有雁的习性 而雁是最为警觉的禽类 他们睡觉时会安排一只雁站岗放哨 我们先是弓着腰前进 但脚底踩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这响声在寂静的雪地里被放大到刺耳的程度 为了使袭击具备突然性 我们趴在雪地上匍匐前进 我们顾不上冰雪扎手 也不怕入湿了棉袄 为了逮鹅 我们是真拼了 在距离团簇在一堆儿睡觉的鹅群数米远时 我们不约而同的一跃而起 扑了上去 鹅群炸开 群鹅鸣叫着奔跑翻滚 我把一只鹅压在身下 为了不让它鸣叫 捏住了它的脖子 我看到解放也得手了 我们提着鹅回到六叔家时 墙上的挂钟正好敲响了十二点 我放下手中的鹅 老曹惊呼道 妈的 这是我家的鹅呀 老曹家的鹅在屋子里乱窜着 嘎嘎的叫着 方妻一把捞住了鹅脖子 然后猛的一拧 老曹踢了方妻一脚 怒骂了一声 六叔道 这是天意 大家笑了几声 但看到老曹那恼怒的表情 便压住了笑声 这时我们才看到 抱在解放怀里的那只鹅 正是那只外号歪把子机枪的鹅霸 他的歪脖子一抻一缩的挣扎着 眼睛闪烁着黑色的光芒 这不公道 老曹说 酒是我出的 鹅也是我家的 太不公道了 解放说 我们家的鹅我下不了手 你们来吧 六叔道 一只就够了 这只歪脖子肉也不会好吃 放了它吧 那不行 老曹说 你们等着 解放把歪头鹅抱到门外去 他将死鹅扔了进来 然后踩着雪走了 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