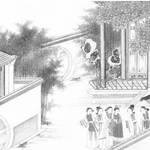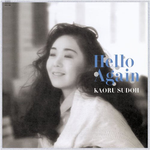本字幕由TME AI技术生成
然后接下来继续给大家讲故事啊
在外三年
思乡的情绪啊
反倒是越来越淡了
这次我从南方回来
不准备在家里待太久
毕竟啊
老婆儿子都在那边
而这边的父母一直啊
有姐姐姐夫照顾
倒也不是十分令我挂心
回到家里啊
刚放下行李
母亲便说
你出外久了
家乡的亲戚老友不免也都生疏了
这次回来
理应啊
逐个拜访
多多走动走动才是
母亲啊
一向最讲究亲情情奋
有时候啊
不免过了头
刚吃罢饭
母亲便要带我去伯父家
其实啊
我伯父伯母早就过世了
家中只有我的一个堂兄
三十多岁了
还是光棍一条
多年未见
甚至啊
连他的长相我都记不起来了
我问母亲啊
应该带些什么礼物才合适
总不能空手而去吧
母亲想了想
说 呃 钱呢
现在她急需要钱
我略改意外
但没有应声
停了一会儿
母亲又告诉我说
你堂兄要结婚了
就在今年年底
到时候啊
能不能从公司请个假
回来参加他的婚礼啊
我仍没有作声
心想他结婚啊
又不是什么大事
有必要这么兴师动众吗
我堂兄结婚的消息啊
令我感到挺意外的
他一直没有结婚
是因为啊
他是个瘸子
但凡条件稍好一点的姑娘都看不上他
母亲把钱硬塞给我堂兄的时候啊
看得出他很感激
末了我们辞别时
他却硬要把我把我留下
说什么兄弟俩多年没见了
应该好好聚一聚
叙叙旧
他是个不善言辞的人
说话容易脸红
我看着他
有点好笑
我和他从来没有什么来往
有什么旧可叙的
看在我母亲的面子上
我还是留了下来
他弄了一瓶劣质白酒
我们啊
边喝边聊
后来他拿出一张照片让我看
他说
那上面的就是他的未婚妻
我一看
简直呆了
上面那姑娘才二十来岁
虽然衣着朴素
但却有着天蝎一般的容貌和身材
我本人的老婆也是中等偏上的姿色
可是跟照片中这姑娘比起来
简直就成了一个黄脸婆
她红着脸征询我的意见
呃
你觉得她怎么样
我没有回答
心想啊
这瘸子怎么还有这么好的命啊
他又告诉我
这姑娘家里很穷
父亲啊
早死了
母亲啊
是个半贪
绅世啊
也挺可怜的
所以才肯嫁给我
我点点头
沉默不语
她又说
哎 你知道吗
她自己也一直患着病
我问 什么病
庞兄回答说
白血病
现在已经换了骨髓
医生说很快就能复原了
我吃了一惊
问道
听说治疗白血病要花很多钱的
堂兄环顾四周
微笑说
所以啊
我把这房子给卖了
现在我只是暂居在这里
等房主来了
我就得搬走
这房子是伯父伯母留给我堂兄的唯一遗产
如今房价节节攀升
估计啊
能卖不少钱
这时啊
我心里想
啊
原来如此啊
我打算明天就回南方了
下午
母亲忽然说
你堂兄的未婚妻今天要出院
你开着你姐夫的车去把把他接回来吧
这几天我都懒得动弹
心里啊
很不愿意去
母亲发觉我都不快
语重心长的说
你堂兄好不容易找个对象
无论如何都要好生巴结着
况且你伯父伯母死的早
除了咱们
还连个依靠帮衬的人都没有
可怜不可怜
说着说着
竟要流泪
见此情景啊
我哪敢不去
临行前我问母亲
哎
我堂兄卖了自己的房子给那姑娘治病
等她病好之后
会不会有什么变故啊
母亲问
什么意思啊
我坦白的说
哎
假如他到时候啊
一脚把我堂兄给踹了
那他岂不是人财两空啊
再说
那姑娘是何样何样的人才
怎么会看上我堂兄这样的残疾人
母亲也十分忧虑
说道 哎
我也正担心这个
但愿那姑娘不是为了钱才同意嫁给少朴的
我心想
这想法真幼稚
来到医院
我终于见到了那姑娘
平心而论
那句奉承女人的话用在这里啊
最合适不过了
她本人啊
比她在相片上还要漂亮
我满脸堆欢的走过去要同他握手
他却无动于衷
毫无反应
其实啊
我堂兄也在场
悄悄走上来告诉我
他看不见人
他是个盲人
这年年底
我并没有回去参加堂兄的婚礼
只是在电话中啊
听母母亲告诉我
堂兄为了给那姑娘治病
不仅卖了房子
还借了一大笔高利贷
结婚之后啊
债主天天上门追讨
堂兄走投无路
甚至啊
想出了卖血换钱的途径
母亲还说
现在也看着他的身体越来越弱
像一具干尸
我伤感而无奈
叹道
还为了娶这一个瞎子姑娘
我堂兄的付出实在是太多了
母亲又告诉我
结婚这才几个月
那姑娘便又住了院
不知道啊
又是得了什么病
听说还需要花一大笔钱
这让你堂兄怎么办呀
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呢
我听了这些
只能承诺
thethe
此后一直再没听到过堂兄的消息
这年入冬
市里啊
来了个残疾人艺术团
艺术团来自内地
经常在全国各地巡演
整司里啊
组织员工观看
哎
我也得到了一张入场券
残障人士的表演大都具有励志效果
整场节目倒也让人心肠澎湃
快结束时
一个女生独唱的节目引起了我的注意
歌唱者容貌姣好
跟我堂兄的那个盲
盲妻长得十分相似
只是我发觉啊
他在台上的一举一动并不像个盲人
好不容易熬到整场结束
我来到后台
找到了先前那个女歌唱者
当时她正在一些观众的拥簇下逐个给他们签名
这证明了她并不是个盲人
我看了她的签名
白雪丽
没错
这就是我堂兄的妻子啊
等到人都散去
我单独找到了他
她并没有认出我
因为她以前可以说是有眼无珠
我向他做了自我介绍
他并没有显出太大的热情
只是淡淡的说
结婚之后
我又做了复明手术
现在已经看得见东西了
我问起我堂兄
他将嘴一撇
冷笑道
啊
当然是在家里了
他一个瘸子
难道还能像我一样四处闯荡吗
这话让我十分不舒服
又试探性的问
当初啊
你做复明手术的这笔费用
是我堂兄卖血得来的
还是他借高利贷得来的
这句话果然刺激了他
他戴着墨镜
却掩饰不住激动的表情
我不知道他当初为什么要给我这些
他明明知道我还不起的
我说
只要你能好好待他
这就足够了
他沉默不语
半晌 冷笑道
你不懂
你压根儿什么都不懂
当晚
我打电话给我母亲
把我御姐白雪丽的经过告诉了她
她沉默许久
终于说道
你可知道
当初那女人是怎样做的复明手术
我迷惑不解
听母亲又说
那女人的失明原来是后天导致的
她现在那只复明的左眼
是你堂兄从自己眼眶里摘出来的
移植给他的
我听了
心里仿佛被揪了一下
说道 他
他怎么那么傻呀
母亲在电话里唏嘘不已
那死
那女人复明不久
就随同那个艺术团去了外地
当初你堂兄并不同意让他出门
为此两人还发生了争执
既然你在当地见到了他
想方设法一定劝他回来
我回答
我试试看
心里却想
如果那女人变了心
九头牛也是拉不回来了
第二天
我来到了那家剧场
得到的消息却是啊
那个艺术团已经离开了这个城市
据知情人士透露啊
他们还要到广州
深圳甚至国外去巡演
无有确切的归期
由于我在公司里业绩出色
很快得到了升迁
被调到东南亚一个国家做销售业务
这薪酬啊
提也提升了不少
谁知在国外一呆就是两年
两年来
经常在电话里听老婆抱怨
他总是说宁愿我在家里一分钱不赚
也不愿这样长期的两地分居
这年临近春节
我终于争取了一个长假
回到国内
带上老婆儿子赶往北方的家乡
这是多年来我们全家的第一次团聚
但是在除夕之夜
母亲啊却写的闷闷不乐
问起缘故
母亲向我说
你去你堂兄家
请他到这里吃年夜饭
还一直一个人在家
怪孤单的
我问母亲
他妻子呢
还没回来
母亲说
你去了就知道了
堂兄看起来啊
老了许多
他的左眼眼眶深泄
里面是一只假眼球
我向他问道
哎
怎么不见我大嫂
他淡淡的说
他走了
以后啊
不会再回来了
我听了无言以对
半晌又安慰他说
哎
这样绝情的女人
不回来也罢
唐兄微笑着说
比哭啊还难看
说道
不是他不愿意回家
而是他不能回来
她死了
我惊声叫道
怎么会啊
他是怎么死的
堂兄却说出这样一句奇怪的话
如果他当初看不见
他就不会死了
原来
早在半年之前
白雪丽就已经辞去了残疾人艺术团的工作
经过在外多年的奔波劳累
白雪丽已经积攒了一笔钱
回到家里
跟堂兄在市区开了一家快餐店
两人虽然一个天蚕一个地缺
但是啊
互相扶持
勉强撑起了一个虽然简陋但却甜蜜的家
可是好景不长
这天夫妻两当晚归
穿过人行道时
一场横祸降临了
当时啊
有一辆卡车从人行道左侧疾驶而来
堂兄摘去的正是左眼
当然毫无察觉
当时白雪丽发现时
情况啊
已经相当危急了
堂兄是个瘸子
行动不便
这时如果白雪丽抛下他
急走几步就能躲过卡车
然而堂凶则必然遭祸
可是事情啊
偏不是这样
那白雪莉当时毫不迟疑
下手狠命将堂兄推出了危险区
而自己本人也失去了躲避的机会
就这样
他被那卡车撞出去两三米远
浑身上下血肉模糊
将他送到医院
因失血过多
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堂兄在他病床前哭道
你真傻
你远可以抛下我自己逃命的
他妻子却笑着说
可是你呢
你什么时候抛下过我
当初你说的那句话
我至今还记得
堂兄说到这里啊
已经是泪眼婆娑
我也是唏嘘而叹
我问
当初你给他说了句什么话
堂兄接着叙述起来
当初我给他捐献眼球的时候
他死活不肯接受
那时啊
我告诉他
任何东西
只要你要
只要我有
想不到这句平淡之语
他临死时都还记得
当晚辗转反侧
深夜不能入眠
忽然接到公司里打来的电话
上司说因有公事需要我第二天便回公司
并且备好行李机票
随时准备奔赴国外
此时身旁的妻子也醒了
并听到了电话的内容
眼泪汪汪的看着我
说道
别走
别那么快离开
我们两年多没相聚了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陪在我身边
我低头思索了一会儿
然后挂上了电话
我答应你
我向他微笑道
只要你需要
只要我拥有
好了
这就是堂兄的故事啊
虽然不恐怖
但是挺感人的一个故事啊
欢迎大家来听故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