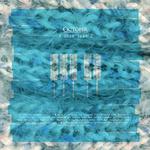本字幕由TME AI技术生成
这十五个六月之内
我心里非常的不安
睡不着觉
老是做可怕的梦
经常从梦中惊醒
白天心里充满了焦虑
夜里经常梦见杀野人
梦见我所以杀野人的正当理由
所有这一切现在暂不提
据说到了五月中旬
依照我那糟糕的木头日历来算
大概是五月十六号
对
就在五月十六那一天
刮了一整天的大风
又是闪又是雷
一直到夜里还是风雨交加
搞个不停
我也说不清事情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只是记得我正在阅读圣经
并且正在认真的思索着我当前的处境
忽然出乎意料的听见了一声枪响
仿佛是从海上发出来的
这个出人意料的事件实在是和我过去所碰到的任何事件在性质上完全不同
因为这个事件在我头脑当中所产生的反应是另外一种性质的
我很快的跳了起来
转眼之间就把梯子竖在半山上
等到半山以后
跟着把他拉起来
第二次爬上梯子
上了山顶
就在这一刹那
我又看见了火光一闪
告诉我第二枪又响了
果然
半分钟以后
又听见了枪声
从那声音知道
它是从上回我坐船被急流冲走的那一带海上传来的
我马上考虑到
这一定是什么船只遇了险
而且同这只船搭伴航行的还有别的船只
因此放这几枪做求救的信号
我这个时候心里倒很沉着
想到
虽然没有办法援助他们
也许他们会援助我吧
于是我就把手头所有的干柴都收集在一块儿
堆成了一大堆
把它放在山上点起来
这些木柴都是干透了的
很快的就燃烧起来
虽然风力很大
还是烧的很旺
我敢说
只要海里有船
他们绝对是看得见无疑
他们是看见了
因为我的火烧起来以后
马上又听见了一声枪响
接着又是好几声枪响
都是从同一个地方传来的
我把火烧了一整夜
一直烧到天亮
等到天一大亮
海上开始晴朗的时候
在远远的海面上
再倒的正东
我仿佛看到个什么东西
至于是帆是船
看不清楚
甚至用望远镜望去都没有办法
距离实在是太远了
而且当时天气仍旧带着雾气
至少海面上是如此的
那天一整天
我不断的眺望着那个东西
不久就看出它始终停在原处
动也不动
于是我就断定
那是一条下了锚的大船
我急于想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
就把枪拿在手里
向岛的南部跑去
跑到我上一回被急流冲走的那些岩石的前面
到了那里
天气已经完全晴朗了
我一眼就看出来
有一只失事的大船昨天夜里撞在我前次驾州出游的时候发现的那些暗礁上了
说起来
这些暗礁由于挡住了急流的冲力
造成了一种逆流
曾经帮助我从生平最绝望的险境里逃出性命
由此可见
一个人的安全很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的毁灭
据我想
这些人可能由于地形不熟
同时又由于那些礁石都是隐蔽在水底下的
再加上昨天晚上东北风刮的急
所以就在晚上触在了礁上
假如他们看见了这个岛
他们必然会设法利用他们的小船上岸上逃走的
可是他们却鸣枪求救
尤其是看到我的火光以后
这件事儿使我不禁产生了种种的想法
首先 我猜想
他们看到我的火光以后
就立时上了小船
尽力的往岸上滑
可是当时风浪很大
把他们卷走了
一会儿我又猜想
他们的小船说不定老早就丢了
因为这种事是屡见不鲜的
尤其是碰到了惊涛巨浪
浪冲打着船只的时候
人们常常是不得把船上的小船拆散
甚至把它扔到海里去
一会儿我又猜想
跟他们搭伴同行的
或者还有别的船
见到他们出事的信号
已经把他们救了起来
载走了
一会儿我又猜想
他们说不定已经坐上小船下了海
给我上回碰到的那股急流冲到大海里去了
到了大洋里
他们就只有受苦和死亡的份了
说不定他们这个时候已经快要饿死了
到了人吃人的地步
所有这些想法
至多不过是我个人的猜测罢了
我现在真的是自顾不暇
除了眼睁睁的看着这伙可怜的人们受苦受难
从心里可怜他们之外
一点办法也没有
可是
这件事对于我也产生了好的影响
那就是从这件事我体会到
更应该感谢上帝
感谢他给了我这么多的照顾
让我在这种凄凉的环境里过得这样的幸福
这样的舒服
同时也感谢他
在整整两船人的中间
只留下我一个人死里逃生
另外
从这件事我又体会到
不管上帝把我们投进怎样恶劣的生活环境
怎样巨大的不幸
总叫我们亲眼看到一些值得感激的事情
看到有一些人的处境比我们还不如
就拿这伙人来说吧
我简直是看不出他们中间有任何人能够逃出性命
同时也找不出任何的理由指望他们不同归于尽
我看到这种光景
心里忽然产生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应应求有的强烈的要求
有的时候
我不禁脱口而出的大声疾呼
天哪
哪怕有一
两个
哪怕只有一个人从这条船逃出性命
跑到我这儿来呢
也好让我有一个伴侣
有一个同类的人说说话
交谈交谈呐
我多年来过着孤寂的生活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的渴望有人往来
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切的感到没有伴侣的痛苦
我多么渴望着有一个人逃出性命啊
哪怕只有一个人
这句话在我口上至少念了一千遍
每逢我这样念的时候
我总是按耐不住心头强烈的要求
把两只手捏的死紧
同时我的上下牙也咬得死紧
半天都不松开
这个时候
海上风平浪静
我很想大着胆子坐小船到那条破船上去
因为我相信一定可以从船上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同时还有一种动机更加有力的推动着我
那就是希望船上还会有一两个活着的人
如果有的话
我不仅可以搭救他的性命
而且在搭救他以后
对于我个人也是一种无上的安慰
这种思想时时刻刻的盘踞着我的心头
使我昼夜不得安宁
一心想坐小船到那个破船上去
在这种念头的支配下
我急忙跑回我的城堡
进行航行的准备
拿了一些面包
一罐清水
一个驾驶用的罗盘
一瓶甘蔗酒
一满楼的葡萄干
我把种种必要的东西都背在身上
走到我那小船的旁边
把船里的水淘干净
使它浮了起来
把所有的东西都放了进去
又跑去拿别的东西
第二次我拿的是一大口的米
还有那把挡太阳的伞
又拿了一大罐子的清水
两沓面包或大麦饼
一瓶羊奶
一块烙干
我费了不少的劲儿才把所有的东西运到小船上
然后一面祈祷上帝保佑我一路平安
就开了船
最初我一出海就朝正北走
走了没多远
就走进了那股向东流动的急流
被他冲着向前飞时
可是速度却没有上回岛南边那股急流那么大
使我完全掌握不住小船
我以桨待舵
使劲的掌握着方向
朝着破船飞也似的驶去
不到两个小时的功夫
就到了他的跟前
我的面前展开了一片凄凉的景象
从那条船的构造格式看来
是一条西班牙船
船身被夹在两块礁石的中间
夹得很紧
船尾和后舱都被浪头打碎了
至于那搁在礁石中间的前舱
由于撞的太猛了
前围和主围都已经倒在甲板上折断了
但是它的斜墙还是好好的
船头看起来也还牢固
我到了船跟前
船上忽然出现了一条狗
它看见我就吱吱的叫起来
我呼唤了它一声
它就跳到海里
游到我的小船这边来
我把他拖到船上
只见他已经饥饿的要死了
我给了他一块面包
就大吃大嚼起来
活像一只在雪里饿了两个星期的狼
我又喂了他一点清水
看那个样子啊
只要我让他尽量的喝
简直就是可以喝的胀破肚子
接着我就上了大船
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两个淹死的人
他们躺在厨房里
也就是钱仓里
紧紧的搂抱在一起
看样子船触礁的时候
海上正起着狂风暴雨
海上波涛汹涌
不断的打在船上
打的人们实在是受不住
同时那海水又不断的涌上来
仿佛把人埋在水里似的
活活的把人闷死了
除了那条狗
船上没有一个活着的生物
同时我在船上看到的货物
没有一件不是让水给泡坏了的
只有放在船舱下的几桶酒
因为水已经退了
漏在外面
可是桶太大了
没有办法移动
我又看见了几只大箱子
搬了两只运到小船上
至于里面装的什么
我也没有功夫去检查
假如触礁的是船尾
受伤的是船的前部
我倒不至虚死一行
因此
根据我从这两只大箱子里找到的东西看来
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断定
船上有很多的财富
同时
根据这只船所走的航线
不难看出
它是从南美巴西附近的布伊诺斯爱丽丝或者是里约拉巴拉他开出来的
准备开到墨西哥海湾的哈瓦那去
再从那里到西班牙去
船上无疑载着许多的财物
但是这些财物目前对任何人都成了无用之物
至于船上其余的人都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完全不清楚
除了这两只箱子
我还找到了一小桶酒
大约有二十加仑
费了不少的劲儿才把它运到我的小船上
舱室里还有几支短枪和一支盛火药的大脚桶
里面大约有四磅火药
短枪对于我毫无用处
因此我仍旧把它留在船上
只是取了盛火药的脚筒
我又拿了一把火铲和一把火钳
都是我极端需要的东西
另外我还拿了两把小铜壶
一个煮巧克力的铜锅和一把烤东西用的铁把
刚好这个时候潮水开始往回流
我就载着这些东西和那只狗离开了
当天晚上
我极端疲惫的回到岛上
当晚我在小船上安歇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
我决计把我所弄到的东西放在我的心洞里
不带到我的城堡里去
我先吃了点东西
然后把全部的货物运到岸上
仔细的检查一下
我弄到的那桶酒
原来是一种甘蔗酒
却不是我们巴西的那种
简单的说
一点儿不好
可是当我打开那两只大箱子的时候
却找到了几样对我大有用处的东西
比如说
我找到了一只很别致的小酒箱
装着几瓶上等的提神酒
每瓶大约有三品托
瓶口上包着银子
又找到了两罐上好的蜜饯
因为口哨封的很好
没有被咸水泡坏
另外呢
还有两罐却已经被水泡坏了
我又找到了一些我求之不得的东西
那就是很好的衬衫
另外还有一沓半白麻纱手帕和有色的领巾
这里面麻纱手帕是我求之不得的东西
热天拿来擦脸
再爽快没有了
此外
我打开箱子里面的小抽屉
又找到了三大口袋的西班牙币
大约有一千一百多枚
其中有一口袋有六块西班牙金币和一些小块的金条
是用纸包着的
估计起来大概有一磅重
在另外的一只大箱子里头
我找出了许多衣服来
但是都是没有用的
看情形应该是属于副炮手的
不过箱子里并没有火药
只有两棒压成了细粒的火药
装在三只小瓶子里
据我猜想
大概是准备装鸟枪用的
总的来说
我这趟出海
弄到的有用的东西实在是不多
至于钱币
对我是简直毫无用处
在一位船员的大箱子里
我又找到了五十多枚西班牙银币
却没有金币
我想这只箱子的主人一定比较贫寒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把这些钱搬回了山洞
按照过去处理那些从我们自己船上搬下来的钱的办法
把他们好好的收藏起来
可惜的是
我没法染指这条大船的另外一部分
因为我确信
如果我能进入那一部分
我一定可以运他几独木船的钱回来
就是有一天我能逃回英国
这些钱摆在这里也相当的妥当
等将来有机会回来
再来搬取也不迟
我把全部的东西搬到岸上
收藏妥当以后
就回到我的小船
把它沿着海岸划回他的旧港
把它拦好
然后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了我的老住处
到了那里
只见一切平安无事
于是我就开始休息
并且照着老样子过日子
照料着我的家世
我在这种情形之下生活了将近两年
我那倒霉的头脑仿佛生来要折磨我似的
在这两年里一直在东打算
西计划
盘算着怎样离开本岛
有的时候
尽管我的理智明明告诉我
那条破船上早已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冒着风险出海了
我还是不死心
总想再去一趟
有的时候我盘算着这边走走
有的时候我又盘算着那边荡荡
我敢说
如果我从萨利出来的时候坐的那条小船还在我的手里
我早已经坐着它出了海
不知去向了
一般人往往有一种通病
就是对于上帝和大自然替他们安排下的生活环境经常不满
照我看来
他们的种种苦难
至少有一半是这种病造成的
然有这种毛病的人
大可以拿我一生的精力做他们的借鉴
因为由于我不肯好好的考虑我原来的家境
不肯好好的考虑我父亲给我的友谊的忠告
再加上我后来犯了同样的错误
才落到了今天的这种不幸地步
假使当初造物安排我做了巴西种植园主之后
保佑我不生妄想
我本来可以心满意足的过下去
说不定经过这么多年
我早已经成了巴西可数的种植园主了
不
甚至我相信
根据我在巴西的短短一段时间里取得的进展看来
我早就拥有十几万葡币了
我为什么要把一份上了轨道的财产
一座资本雄厚
蒸蒸日上的种植园丢在脑后
甘愿去当一个管货员
到几内亚去贩黑奴呢
我在家里
只要有耐性
有充分的时间
不是同样可以把资金累积起来
坐在自己的门口从那些黑奴贩子的手里买到黑奴吗
虽说价钱贵一点
但实在是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节省这笔价格的差额
然而
这正是一般少不更事的青年人所常走的道
非要经过多年的锻炼
经过代价很高的阅历
不会明白他是如何的荒唐
我现在总算是明白过来了
可是这种错误在我的性格里已经如此的根深蒂固
因此
一直到现在
我还不能安于现状
还是不断的盘算着采取什么办法
有没有可能逃出这里
为了使大家对我后面的故事更感兴趣
我觉得不妨先叙述一下我这种荒唐的逃走计划最初是怎样形成的
后来又是怎样实行的
以及在什么基础上实行的
我从破船上回来以后
从表面看起来
我已经在城堡
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我的小船已经照原来的样子安置在水底下
我的生活已经恢复了从前的状态
那是我来到这个孤寂的海岛第二十四年的雨季的三月
一天夜里
我躺在我的吊床上不能入睡
我很健康
无论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没有一点病痛
没有一点不舒服
可是我怎么都合不上眼
睡不着
简直可以说一个晚上连一个盹儿都没打
专门胡思乱想
要把那天晚上像旋风似的掠过我的记忆的无穷无尽的思想都记录下来
不仅是不可能
而且也不必要
我把我一生的历史大略的回顾了一下
从早年起
一直到我来到岛上
一直到我来到岛上以后的生活
我回想到我来到岛上以后的情况时
我把最初几年住在这儿的快活日子和我见到沙上脚印以后那种焦虑
恐惧
小心翼翼的生活做了一番比较
我不是不清楚多少年以来
那些野人曾经不断的到岛上来
甚至曾经成千成百的登过岸
但是过去既然不知道这件事
当然也不会担惊害怕
尽管我的危机照样存在
我的日子却过得十分美满
我觉得自己不知道有危险
就跟自己压根儿没有被危险所包围一样幸福